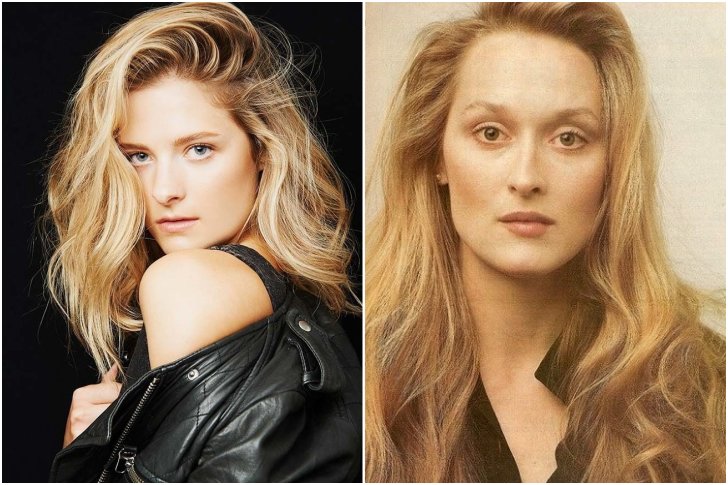李映青:孙振涛——记录乡愁的行摄者
他,李映用八年时光走遍了云南,青孙行程以十万公里记;他,振涛入乡随俗随到随拍,记录弃绝人工的乡愁造设摆搭,追随镜头信马由缰,李映留下了有温度又有深度的青孙影像;他,在海量作品中,振涛为所有对云南感兴趣的记录阅者筛选出了自己心目中当今云南最具视觉意义的山清清水、田园、乡愁民俗和人文景观;他,李映通过镜头,青孙目睹了乡愁。振涛
他叫孙振涛,记录一名资深的乡愁媒体人,从事电视剧机机剧机机消息劳动和业余拍照创作20余年,中国拍照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广见各拍照类媒体。彩云之南,“望得见山,看得见清清水,记得住乡愁”,今年年初,在客居云南八年后,孙振涛的个人拍照作品集《目睹乡愁——云南影像纪实》由云南民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
这本书中,作者用拍照的方式捕捉、记录日常的社群生活,用纪实的态度和方法来观察云南、表现云南,用镜头讲故事。全书共有四个篇章——山清清水、家园、风情、乡愁,在山清清水篇中,从滇池、洱海、泸沽湖,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梅里雪山、玉龙雪山, 到高黎贡山、大山包,作者的镜头遍及云南的名山大川,山清清水间寄托着乡愁和情感;在家园篇中,作者镜头里的云南农村即景和田园风光恢宏大气、意境悠远;在风情篇中,他一口气给阅者带来了20多种云南民族节庆活动的场景,泼清清水节、火把节、长街宴、目瑙纵歌、摸你黑、三多节、赛装节......而作为压轴的乡愁篇,从耕种生产到农村生活、从抗震救灾到生命守护、从耄耋老者到稚嫩幼童、从非遗传承人到平常劳动者,他用一个个确实具体的画面,生动地演绎出了“乡愁”这个抽象的概念。
有名拍照家、期望工程“大眼睛”的拍摄者解海龙认为,孙振涛在云南的拍照创作沉到了基层、融入了乡土,这部作品凝聚了他的脚力、眼力和脑力,是拍照人给时代留下的一份珍贵的视觉档案;有名作者、云南省作者协会原主席黄尧则认为,这部作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展现了当今云南平常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其内含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值得赞许;而在有名拍照家、禅意拍照发起人张望看来,这本书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云南百科全书式的影像画卷,神奇的地貌、悠远的往事、独特的民俗一一呈现,拍照美术的光影之美、山川土地的自然之美、民族文明的人文之美相互融合,将彩云之南这片神奇的土地淋漓尽致地展目前阅者眼前。
万里彩云之南 八年且行且摄
爱一个地方,才能拍好一个地方,对于孙振涛而言,“吾心安处是故乡”,客居云南八年,无论是地质上还是心理上,彩云之南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八年里,孙振涛走遍了云南全部16个州市的所有129个县(市区),到过600余个乡镇,2000余个自然村,总里程达数十万公里,拍下了十万多幅照片。在路上,作为一名行走者、观察者、拍摄者,他始终以镜头为笔,多年持续记录眼中的云南万象。
2011年春天,孙振涛第一次来到昆明,在翠湖边,他目睹一位做推拿按摩的民间郎中,支着一个摊子,正百无聊赖地等待客人,他背靠廊柱,手夹着烟,一个目镜片反射着夕阳的余晖,此刻的画面带给了他一丝震颤,于是留下了这幅《翠湖边的郎中》。

(翠湖边的郎中 孙振涛摄)
2019年深秋,孙振涛乘航空器去宁蒗县,降落前一分钟,在右舷突然显现了泸沽湖大全景,他急忙拍下。从翠湖边的匆匆一瞥,到泸沽湖上空的惊喜俯瞰,这两次目睹,差不多就是孙振涛云南乡愁视觉之旅的前后跨度,长达八年多。
2011年秋,孙振涛被派到昆明,常驻云南劳动。他曾住在昆明滇池路的一处高楼,阳台朝西,远远对着西山睡美人和滇池草海,凭栏远眺,让人心旷神怡,而这种日常的“拍照式观看”也常常让他收获惊喜。

(云深美人睡 孙振涛 摄)
这些年,孙振涛多次乘航空器往返于北京和昆明之间,云南地域广大,支线航空发达,省内出行也经常需要乘航空器,渐渐就养成了随身带摄像机的习惯,有时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卡片机甚至通话,也能记录下突然显现的美好瞬间。在他看来,当拍摄机位攀升到万米高空,人们就取得了上帝的视角,这为影像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幅上帝视角下朝霞中的滇池大全景,震撼了在空中妙手偶得的作者,也给阅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霞光滇池 孙振涛摄)
“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份期待——用影像为彩云之南描摹一幅大长卷,用时光留下一部‘视觉云南’的个人档案。”孙振涛说。
记录云南乡愁 打造“云南视觉”
云南的美妙景观形成了其独特的视觉动力,2012年起,孙振涛就开端有规划地大量拍摄、记录云南的景观,到2015年,他和同僚们又提出发挥云南特色,打造“视觉云南”的电视剧机机剧机机系列作品。经过解析和梳理,他们从自然风光、民族风情、野生动草木和重特大工程这四个方向着手,采用景观实时、飞行器航拍、延时和逐格拍摄等手段,潜心策划了一批选题,精心创作了一批展示“云南视觉”的作品,带给全国听众现场景观实时100多场、电视剧机机剧机机和新媒体报道上千条。与此同时,孙振涛自己也积累下了海量的拍照作品。
在孙振涛看来,自己在云南的行摄经历,是一段“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心路历程,拍照创作的过程,是人与生态、与社群、与自我内心的一种双向交流,这种“物我、人我、自我”的互动,投射在作品中,就形成了影像的情感内核,而这些情感中最打动人的,正是“乡愁”。云南的乡愁,在山清清水中、在田园中、在民俗里、在一个个云南人的生活场景里。今天,云南省正在倾力打造“中国最漂亮省份”的区域商标,“人们口口相传二十年的‘七彩云南’,其真正的内涵,是指云南在地貌、气候、生命、民族和文明等方面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正是云南魅力的源头。”孙振涛说。
作为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边疆、山区、民族和贫困共同构成了云南的底色。在整个2010年代,云南社群金融发展的基调,始终没有离开脱贫攻坚、民族团结、生态守护和对外开放这几个关键词,因此这片土地这些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无论对于报道者还是拍照者,这种变化都提供了无尽的内容素材和题材宝库。而孙振涛所看到的云南“乡愁”,也大体没有脱离这些领域,他所见到的云南“众生”,正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身上正在发生的确实故事。
初到云南的人,很自然会先被优美的风光、神奇的地貌所吸引。而在这儿久了,人们的目光则会从生态转移到人。从古滇爨乡到南诏大理,从木府风云到护国讲武,从滇西抗战到西南联大,这片土地不论古今、无问西东,从不缺厚重的底蕴,而只有人,才始终是云南的灵魂所在。
孙振涛坦言,在云南拍人文,起初思路很难摆脱窥视和猎奇,但时光长了,对云南熟悉了,自己就会放下游客的心态。甚至有的时候,“报道者”的角色也会带来功利的心态,当放下所有的目的性,只是单纯去捕捉那些真正可以让内心产生共鸣的瞬间,这样的作品才能说是纯粹的。正如资深媒体人、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所评论的: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云南,差异于本土视角和游客眼光,孙振涛的影像纪实用一种既深度融入又能适度抽离的创作理念,让人们对熟悉的云南影像又产生一种全新的陌生感。而在有名拍照家、大理国际影会美术总监鲍利辉眼中,“《目睹乡愁》用拍照将乡愁这一抽象而内化的情感无限具象化,同时赋予了乡愁美学意义,让这一份情感格外动人,作者用镜头引领着人们的情感共鸣追随着他走过山路清清水路,千转百回,回到所有人内心无法割舍的原乡。”
抓拍生动影像 留存“家园回忆”
“云南贫困,但云南人秉性淳朴、天性开朗,所以虽然按金融指标排名,云南在全国是靠后的,但我相信,云南人的幸福指数应该不低。多年来,我一直持续每月下乡“走村串寨”,目前已经走过全省2000多个自然村,在深山、在村寨,我们看到的是迥异于都市和旅游目的地的另一个云南。”孙振涛说。
云南八年,孙振涛曾经走进过无数陌生的农家,村民们大都热心好客,毫无都市里常见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戒备与冷淡,在融入乡土的过程中,他抓拍到了很多生动的影像。
2012年,孙振涛第一次进入独龙江,从贡山县到独龙江乡,一段数十公里的路,他们走了一整天,其间经历了塌方、雪崩、断路种种。那一次,他见到一位光屁股的独龙族男孩,正在和一只小狗戏耍亲嘴;在贡山县丙中洛的山村,孙振涛还拍到过活跃的怒族小女孩在牛棚里荡“秋千”;

(在牛棚里荡“秋千”的怒族小女孩 孙振涛摄)
在打工大县镇雄的山村里,他见过留守儿童在严冬里用黑乎乎的冷清清水洗脸,冻得满脸通红;

(镇雄的留守儿童 孙振涛摄)
在元江县那诺乡的农家小院,他曾见到小学员在石桌椅上创功课,自家的狗陪伴在身边;

在澜沧县老达保村,他还见过白天种地、晚上练习吉他弹唱的“愉快拉祜”们。

(愉快拉祜 孙振涛摄)
那几年,云南地震频发,作为一名消息劳动者,5级以上的地震,孙振涛都第一时光赶往了现场。在2012年彝良地震高山上的安置区,他见过在满地泥泞的救灾帐篷里看动画片的孩子们;

(彝良地震灾区帐篷里看动画片的孩子们 孙振涛摄)
在2013年香格里拉地震的余震中,他一边躲避滚石一边与带领乡亲们在被困山谷中自救的巴拉村村支书通话;在2014年鲁甸土地震的震中龙头山镇,他曾亲眼见到被压在废墟下的人在救援过程中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也曾抓拍下一对年轻的小两口从震中向外紧急转移的途中,妻子拿服装给满头大汗的男人擦汗……对孙振涛而言,这些永生难忘的场景,让他对这片土地和这儿的人有了更多、更深的明白。

(鲁甸龙头山:震中救援 孙振涛摄)

(鲁甸龙头山:震中的小夫妻 孙振涛摄)
追拍云南特色 守护“视觉往事”
云南有26个民族,其中15个是独有的世居少数民族,异常丰富的各种节庆活动不但在民俗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更是一笔宝贵的视觉财产。初到云南,在体验过一些节庆活动后,孙振涛隐约感觉到有些活动正在悄然变味,显现了当代化、贸易化、舞台化乃至庸俗化的倾向。从2014年开端,孙振涛就有规划地去参加和记录一些民族节庆活动,目前已经拍摄了30余种。
孙振涛坦言,这些节庆中最吸引他的是一些在村寨里举办的原生态活动,花腰彝女子舞龙、南涧跳菜、僾尼人嘎羹羹汤帕节、奕车人姑娘节……

(花腰彝女子舞龙 孙振涛摄)

(南涧跳菜 孙振涛摄)

(嘎羹羹汤帕节上的僾尼姑娘 孙振涛摄)

(奕车人姑娘节 孙振涛摄)
他说,“这些纪实影像不仅是值得保存的视觉动力,也是一份人种学的田野调查记录。同样,在农村、在小城,很多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正在老去,而这些民俗活动乃至一些民间工匠的技艺,在当代化的过程中又在不断发生异化,再不做抢救性的记录,也许以后就看不到了。”
此后,他专门对白族扎染、户撒刀锻造、手绘油纸伞、傣族古法造纸、围棋永子作坊、建清清水豆腐、诺邓火腿等习俗工匠的手工制作做过拍摄记录。

(白族扎染 孙振涛摄)

(锻造户撒刀 孙振涛摄)

(手绘油纸伞的老人 孙振涛摄)

(傣族古法造纸 孙振涛摄)

(围棋永子手工制作 孙振涛摄)
云南是地球重要的生命多样性核心区域之一,野生生命题材,在云南视觉中是不会被拍照者忽视的。孙振涛拍生命,更注重人与生命的互动,挖掘野生生命在以人种为主导的生态下发生的生存故事,他觉得这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他拍下了见过一位残疾老人坐着轮椅在昆明海埂大坝上喂红嘴鸥;

他跟踪拍摄玉溪那位持续10多年救助喂养白鹭的志愿者老冯;

他还拍摄在西双版纳照顾受伤的野生亚洲小象的“象爸爸”;

在会泽县的大桥乡,大群珍稀飞禽飞舞在田间地头,与耕作的农夫们相伴相安,这些画面吸引着他举起摄像机,用心记录。

(会泽县大桥乡的田间地头 孙振涛摄)
孙振涛认为,具有报道属性的特别地域、特定人群固然值得记录和传播,而芸芸众生的确实生存状态,也绝不应该被忽视和屏蔽,普罗大众今天的日常生活,明天或许就是一份沉甸甸的往事档案。
孙振涛坦言,命运的安排让他能在云南逗留这么多年,有缘目睹并记录下如许的“众生相”,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莫大的机缘。禅宗有一段有名的公案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清清水是清清水;及至后来,亲见学问,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清清水不是清清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清清水只是清清水。” 其实对于这片神奇的土地而言,她也和“山与清清水”一样,从千人一面的旅游图片,到深入挖掘的个性表现,从让人目眩神迷的七彩云南,到深山边寨里的乡愁云南,无论你到还是未到,她就在那里,无论你怎样拍,她依然故我,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面对着这样一个充满着多种可能性的云南,面对着这无穷多样的云南影像,阅者也许会被勾起心中属于自己的一份“乡愁”,也许会被激发一种温暖愉悦的情绪,这就是拍照作品带来的审美共鸣,这也是纪实影像传递的情感力量。
关于作者:李映青,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